世纪之交,人们似乎进入这样一种时空:一个充满期待的时刻,一个让人频频回首的关口。回望重庆百年来路,有太多太久的人和事让人感叹,追忆。然而最先涌上心头的,却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不可忘却的重庆人——邹容。
1885年,重庆夫子池洪家院子中,一个男孩呱呱落地。他,真是生不逢时。那是一个绝望的年代:内忧、外患、割地、赔款……落后的悲哀笼罩着每一个中国人。然而,觉醒总是从痛苦的黑暗中产生的。苦难,造就了一代英雄。如同广东有孙中山、浙江有章太炎、湖南有黄兴一样,重庆也走出了少年邹容。1901年深秋的一个早上,出身富商家庭却偏爱读《天演论》,吟诵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邹容,终于舍去父亲为他铺就的黄金路,毅然踏上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这时的他,已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并深知,振兴民族的希望不可能来自对“文明古国”旧梦的重温,而来自一种痛苦的向敌国的学习。1902年,他从上海到了日本。 此时的日本,既是我们痛恨的敌国,同时又是中国学生接近西方新学的“捷径”。邹容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同时又如饥渴地攻读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法国革命史》和《美国独立宣言》。他开始反思:为什么同是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和“救国图存”的维新变法都最终归于失败?他开始把学习的目光,从前人只注重纯技术、纯科学,逐渐转向政体、方法论和世界观。“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一年后,苦苦寻求的邹容终于为中华民族探索到一条复兴之路。他的惊世之作《革命军》诞生了。这时,他才18岁。
1903年5月,《革命军》在上海正式出版。该书一发行,立刻引起了极大轰动。正如当时上海进步报刊《苏报》所言:“笔极犀利、文极沉重,读这无不拨剑起舞,发冲眉竖。”“此诚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革命军》告诉人们:中国的改革再也不能老是包容于宽大的封建龙袍之中,“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老调”都只是解救一姓一朝封建统治的强心剂,而不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要救中国,路一条:革命。而革命的目的:用暴力推翻腐朽专制的清王朝,扫荡“外来之恶魔”,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8岁的邹容,是第一个向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权公开宣战,第一个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定了详细纲领的人。西方科学在他的手里,再不是一把匠人的凿子,而正变成革命者思想的火炬。
“号角一声惊旧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人们争相传阅《革命军》,使之在短短的几年中,竟再版20余次,发行量高达110多万册。为此,清政府惊恐万状。 1903年6月30日,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共同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苏报案”,邹被捕入狱。两年后,年仅21岁的他不幸病死狱中。
历史是寄情于未来的。就在邹容含恨死去的第六个年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邹容当年描绘的共和国的蓝图,终于被《革命军》唤醒的革命党人画在了中华的大地上。
邹容已离开我们近一个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转折。然而,不论何时何处,当我们追述封建皇宫坍塌的那一特定的历史瞬间时, 便一定会记起邹容,记起那如雷霆之声的《革命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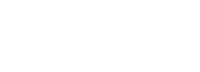

 1027
1027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