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约三百米外,有一处十几步的青石台阶,拾级而上,是一块空旷的大平坝,另一端是一排灰色的平房,这就是“红岩托儿所旧址”。站在屋前向远处望,郁郁葱葱,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邓颖超同志的指示下办了这个托儿所,邓颖超对托儿所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与心血,红岩的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的童年。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以钱之光为处长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相继成立,中央先后从武汉、贵阳等地抽调了一大批年青的同志来此工作,当时工作人员有一百人左右。随着时光流逝,大家陆续成家生子。当年的办公条件比较简朴,办公室兼具宿舍功能。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和一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二楼,三楼住的是电台工作人员,一楼是行政人员,紧张的工作却时不时被孩子的哭闹打断,孩子哭声一起,四邻不安,大人急得没法就打孩子,可越是这样,孩子哭闹得就越厉害,做父母的又心疼又心烦。
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没有孩子,但他们比谁都更关心孩子们。为了解决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在邓颖超的提议下,托儿互助组于1942年春成立了,孩子们被集中起来由妈妈们轮流看管,大家轮流值班,这样其他人就可以安心地工作了。后来互助组的孩子日益增多,于是就在办事处楼外三、四百米的几间小平房办起了托儿所,并安排了专职人员到托儿所工作。
当时托儿所有三十几个孩子,年龄参差不齐,从几个月到五六岁不等,分成三个班,初生几个月的婴儿放在箩筐里,再大点的就放在小木床上。由于人手少,没有经验,托儿所又缺乏玩具,孩子们只好玩土,衣服弄脏了有时没换的,只好光着屁股,妈妈们来接孩子时自然不高兴,而托儿所的专职妈妈也很不痛快,累了一天,腰也酸、背也痛,最后还没落个好。
托儿所的问题多,大有办不下去之势。邓颖超为了解决托儿所存在的问题,召集妈妈们开会。她首先肯定了托儿所的性质是“合作社”,把孩子入托比喻成入股,她说要送孩子进托儿所,就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力。托儿所现在无论是人力物力上都有很多困难,所以必须依靠每个孩子的家长关心了解和帮助托儿所工作人员,共同努力才能办好。在会上她向妈妈们提出了具体要求:每人每周要到托儿所值班,带孩子一至两个半天。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给托儿所增加力量,二是具体了解托儿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便于改进托儿所的工作。为此托儿所决定每月小结一次,每季度全体妈妈们总结一次,每半年总结一次并报送延安。大家一听要把总结送到延安,更是兴奋,觉得这是党对自己工作的重视,学文化、学业务的热情高涨,动力十足。
托儿所开办之初,缺少玩具,只有一个滑梯和一个自制的秋千、一个翘翘板,孩子们常因轮不到玩而哭闹,有时因此而打架。为了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托儿所有针对性地编了不少儿歌、顺口溜和故事,还教孩子们演戏、跳舞、画画,讲天文知识等。但孩子毕竟喜欢新颖的东西。得知这一情况,心系托儿所的邓颖超动员办事处的同志们,她说,孩子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大家都要关心。没有玩具,那就动手做吧!于是同志们一齐动手做了许多玩具,有手枪、冲锋枪,还有大小卡车、动物车、推土车等。妈妈阿姨们也做了布娃娃、线布球、踺子和各种叠纸。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二种玩具,玩得更欢了!
尽管工作繁忙,邓颖超仍抽空关心托儿所,她认为带孩子要研究和了解儿童的心理,还找了一些有关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孩子方面的书籍让妈妈们学习,并告诉她们,不要大人喜欢什么就让孩子干什么,要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和特点进行教育。
先后在托儿所待过的孩子大约有30多个,其中有位外号“小乐天”的孩子是荣高棠和管平的大儿子,他在几个月大时就随父母来到红岩,是同志们的开心果。因为他非常爱笑,周恩来说他是个乐天派,就管他叫“小乐天”,管邓颖超叫“大乐天”,自号“赛乐天”。有一次当小乐天跑到大门口迎接大乐天时童小鹏给他们照了像。周恩来就用这张相片向办事处的墙报投了稿,并赋诗一首:“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上款是“题双乐天图”,下款是“赛乐天题”,从此小乐天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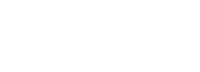

 827
827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