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3日凌晨,地处抗战前沿的长沙突然全城起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余火燃了十来天。经此大火,长沙顿成焦土,军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无以计数,价值无法估量,几十万人流离失所。
长沙大火举世震惊,人们纷纷探究起因。原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11月初日军逼近长沙,国民政府军委会制订了对长沙实行焦土抗战的战略,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1890—1969)就此进行了布置和安排,准备待日军兵临城下之际,全城拉响空袭警报,使军民疏散,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全城同时举火。不料,11月13日凌晨,日军尚在长沙一二百里之外行止未明,焚城条件远未达到,无任何征兆就全城起火了。事后最高军事当局组织的军法会审调查的结果,也无法确切说明究竟是谁下令放的火,最后以“误信谣言,惊慌躁切,辱职殃民”将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鄷悌等三个直接责任人枪决以平民愤。张治中自请处分,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被“予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所谓焦土抗战战略,在当时抗战阵营内部就对其有不同的观点,真正实施时,时机的把握更是最关键的。长沙大火结果是焦土抗战没抗击到敌人,反而坑害得民众惨烈,民怨沸腾,张治中身为省主席,自然难辞其咎,众矢加身。更有传言纷纷说是张治中下令放火,却推责拿部下当替死鬼的,本来就深自痛悔的张治中其内心压力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告全湘同胞书”中说自己“神明内疚,罪戾实深”;他在呈请去任的电文中表示“腼颜待罪,痛苦殊深”;即便二十年后,“平常做事是提得起,放得下”的张治中,对此事仍是“提不起又放不下”,长沙大火成为他“毕生内疚神明耿耿于心的一件事”。
正当各方对张治中纷纷落井下石,使他感到四面楚歌之时,他却得到了来自中共方面的关怀。长沙大火时,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正在长沙,半夜起火之时,他因工作劳累正熟睡中,幸得勤务兵及时叫醒逃离已着火的房屋才免于葬身火海。大火之后,他立即组织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人员投入救灾中,协助张治中处理善后事宜;周恩来在严正指出张治中应承担责任的同时,还亲笔字斟句酌地为张治中修改关于长沙大火的报端谈话和张治中起草的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联合名义发表的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说明等文稿。
张治中与中共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在黄埔军校任学生军官团团长等职和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共事时,就很钦佩共产党人的学识才干和奋发精神。他虽然忠诚于国民党,却跟共产党人走得很近,被右派指责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张治中极力躲避涉及国共斗争领域,更避免参与反共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张治中在湖南省主席任上恢复了与中共朋友的关系,与中共驻湖南代表徐特立及常到长沙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相处很好,周恩来等也很珍惜与张治中的友谊,尊重张治中的工作,双方共同协力开展抗日救亡事业。这次长沙大火事件,中共朋友的谅解和帮助,使张治中在困境中感受到极大的温暖,他后来回忆道:“长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我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子对我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以慰藉”,“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由此,他更加坚定了维护国共团结抗战建国的立场。在以后的抗战岁月里,周恩来也非常注重对张治中的尊重和团结,双方虽然各持政治立场,友谊却更加深厚。张治中曾自豪地对人说,他与周恩来是几十年的朋友,无话不谈。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积极推动和平建国事业。重庆谈判期间,他亲自护送毛泽东往返延安,还把自己的宅邸“桂园”让出来,提供给毛泽东作办公和会客用;他还和周恩来一起妥善安排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警卫工作,再三嘱咐警卫人员说:“保卫毛泽东,要胜过我十倍!”后来,他又以自己的影响力,积极推动新疆的和平解放和起义部队的整编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一份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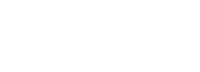

 989
989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