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新华日报》的许涤新与南方局工作的女青年方卓芬恋爱结婚了。这是《新华日报》在重庆成立后的第一对新人,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都非常重视,纷纷向许涤新和方卓芬道喜。
董必武语重心长的对这对新人说:“你们是同志加夫妇,要相亲相爱啊!”一年后,他们爱情的结晶诞生了,一个名叫许嘉陵的小男孩在大家的祝福声中来到人世。
随着孩子的到来,许涤新的工作也繁忙了起来。1940年冬,许涤新从《新华日报》调到南方局宣传部当秘书,负责党报和党刊的编委和撰校工作,同时审查《新华日报》的社论版,把初步意见向周恩来和董必武汇报,再送回报馆送国民党报刊审查委员会审查。国民党扣留的社论,就只好再写再送审查。国民党有时乱改或者一夜之间连续扣留几篇,许涤新和战友们就索性在第一版社论的位置上让它空白,叫做“开天窗”,以示抗议。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需要一盏明灯,而《新华日报》不断提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使人民得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以及游行示威等自由的社论和专论,好比一盏明灯照亮了黑暗的国统区。
1940年12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统战工作委员会下设立经济组,任许涤新为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经济组的任务是宣传党的财政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资料,并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许涤新带领经济组以及潜伏在国民党经济部门的地下党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勤业、勤学、勤交友”,积极开展工作,对我党全面了解国统区的经济状况,加强解放区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经济数据和材料,受到南方局的充分肯定。1942年春,周恩来专门向中央报告,称赞许涤新领导的经济组的工作成绩“为以前所不及”。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工作过度劳累,许涤新以前在国民党苏州陆军监狱所犯的肺结核病又犯了。在当时,治疗结核病没有特效药,病中的许涤新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家庭一切重担都压在方卓芬身上。小嘉陵在几个月大时嘴里老是发出呜呜的响声,于是给他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小火车”,祝愿他能像火车一样奔跑。然而事与愿违,“小火车”在一岁大的时候不幸患上了颈椎炎和骨结核。但是,由于许涤新工作繁忙,“小火车”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奔跑、欢笑,而是穿着笨重的石膏背心,度过了他特殊的童年。
周恩来和董必武见许涤新病成这个样子,命令他停止所有工作,到重庆郊区找个安静的地方修养。在这期间,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和《官僚资本论》等书,这些著作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转变关头,在全国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起到了启蒙作用。
1946年秋天,许涤新夫妇被派去香港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然而许嘉陵病情却更加的恶化,在一家私人诊所照了X光片,腰椎旁边一道白色的脓管和烂了三四节的脊椎骨赫然在目,必须住院动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昂贵的手术费,以许涤新微薄的薪酬是不足以支付的。而当时的许涤新正在负责香港工作委员会财政工作,掌管着巨额的经费。有人建议从公家经费中借出一笔钱,为孩子治病。许涤新夫妇却坚持不肯,他们说:“个人用公家的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宁亏自己,不亏组织。”最后在数位朋友的支援下,凑得400元港币,为许嘉陵交了手术费,但却让许嘉陵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落下终身残疾。而这件事也给许涤新夫妇的心灵上留下永久的伤痛。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1994年、2001年两次在京采访方卓芬时,说及这段往事,老人依然忍不住泪流满面。
2001年,已60岁的许嘉陵仍坐在轮椅上,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感慨道:“由于父母亲在革命战争年代,严于律己,不肯从他们所掌握的百万公家经费中挪出一点点来医治我的病,造成了我的终身残疾,这也是我对革命的奉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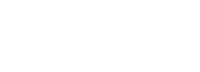

 930
930 分享
分享